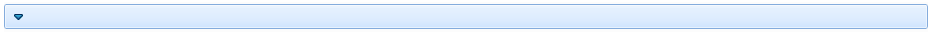请陈独秀孙女吃顿饭
黄亚洲
来京写作已一月有余,写得“手抽筋”之时,忽动念头,邀请陈独秀的孙女来吃一顿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曲线救国”,以表达对陈独秀的一种敬重。历史长河太长,咱够不着,现时的北京饭馆还是够得着的,这一个多月来,天天窝京城小饭馆点一两小菜,几份油腻腻的菜单早都背熟。
未曾谋面的陈红教授很爽快,来短信说“我先生也来行不行”,这种不见外的脾性真令人赞赏。一见面,都是“四零后”,我属牛,她属马,人生做牛做马,话题就多。
陈教授见面就说要为当年的电影《开天辟地》感谢我,说是一份迟了二十年才表达的感谢,这使我汗颜。当然,1991年公映的《开天辟地》,头一回表现了陈独秀的屏幕正面形象,使得那时候的众多中国大陆人吃一惊:“原来陈独秀不是坏人?”说起这些,真是令人扼腕。
问题是现在的许多事情也令人扼腕,虽说过去了整整二十年,虽说在历史的真相方面,许多事情正在浮出水面而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国人的认识程度还是远远滞后,赶不上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很无奈,这是一种政治滞后。
这种滞后是有意造成的,怪不了国人的不智慧。
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但一直是小聪明多,大聪明少。我们中华民族若是一个很成熟的民族,也不至于吃那么大的苦头,弄得一部现当代史如此血肉模糊。当然,现在我们已越来越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聪明,这也是智慧的表现。
谈起四川江津那个“石墙院”,我们的兴奋就溢于言表。我找出一首小诗,当着王镇远陈红夫妇读了一遍。这是我六年前去那里瞻仰后在回程时的小汽车上写的,可见我当时的心绪难平,诗题就叫《江津, 陈独秀乡间客寓》:
在暗黑的小屋里,在门边,遗体放了两天。身上仅裹了几尺白绸,作为灵魂的渡船。
身无分文。长江边一方墓地,也是友人所捐。
而现在,世界上无数的史册和教科书,为了迎接他的载重,都预留了版面。
我们的党史专家们,也已经把许多章节删去,以便让腾出的空白,与白绸的颜色,保持一种关联。
现在想来,思想,真的不是物质的东西。供作思想的营养,有时候,就是时间!
石墙院, 陈独秀倒下的地方,历史的伤痕,至今,没有复原;他在后院种下的那株梨树,已经成人,然而,果实,仍是又青又酸。
当然,既唤作石墙院,便自有一种堡垒的风范:这个世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旗帜,在等待旗杆!城堡的基石,在风中,纹丝不动;山脚下,也始终是长江不死的波谰!
遗体可以抬走,思想没有晚年。
陈教授很同意这首诗的最后两句,也同意“思想不是物质的东西,供作思想的营养,有时候就是时间”这样的表述。
我们对时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我也勉励自己,在以后写到陈独秀的时候,能对这位我最敬重的中国人有更加客观的表达。现在我们的束缚还是那么多,各地的陈独秀研究会不是被解散就是工作得谨谨慎慎,这种状态绝对不是对历史应有的的尊重。
一个很小的例子也可以说明问题的尴尬。那个陈独秀住过的北京四合院,箭杆胡同9号,现今的箭杆胡同20号,也是当年名震全国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一个近乎神圣的地方,现在却还是个住着六户人家的大杂院,而且东房的面积已被“民政部大楼”割走了,只剩一个“门脸”儿;虽说院子门口立有一块牌子,称作是“市一级”的文保单位,但却破旧不堪,已是多年的“四类危房”,一直不见修缮。陈独秀的孙女婿王镇远先生曾经担任过北京市规划局副局长,现今还是市政府参事,以这样的身份多次呼吁有关部门迁出居民、修缮保护,但仍是无所回应。
回应其实是有的,那就是“六户人家的搬迁费用太高”。对一级政府而言,六户人家的搬迁费用能算高吗?是不敢触动历史,历史的面貌动一动太可怕。 是政治,是心理脆弱。是“维稳”,是在历史经年的的溃烂处贴一块无用的“创可贴”,是医术不高。但是我们对时间始终抱有敬意。中国的历史终究会体现中国人固有的智慧。我坚信,“箭杆胡同9号”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北京的一个参观亮点,能以一种“新青年启蒙”的姿态继续疾呼科学与民主,继续轰响陈独秀的那种振聋发聩的呐喊之声。
陈教授赠我一册名为《世纪情缘》的画册。饭毕,送走客人后,我翻阅画册久久不忍释手。我在一幅照片面前差点流下眼泪。那是头发花白的陈红跪在地上的形象,照片说明是:“2008年10月24日陈红到上海龙华烈士公墓祭扫大伯父陈延年、二伯父陈乔年墓。”
我仿佛看见了当年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开会见面互相称同志的一幕。历史是这样清晰,容不得半点模糊啊!
残破的历史,何时才得以彻底的动迁与修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