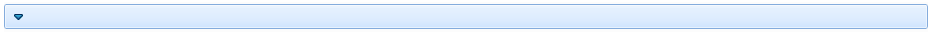1942年5月27日,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创始人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回顾他的一生,如何评价他在大革命中的主张和行为,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上海书评》曾于2013年11月10日刊发过黄道炫对《陈独秀全传》的书评,题为《谁该为大革命失败负责?》,对我们理解这一历史问题颇有帮助。 生活中,历史家的爱大概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不过,历史家独特的职业决定他们还可能有另一种爱。历史家的先生、太太们要小心,在历史家翻检资料、进行人物研究时,或许一个情敌已经悄悄潜入:他的研究对象。 历史研究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职业,一项研究常常要进行几年、十几年乃至一生。由于长期浸润,历史家在研究人物时,不免会日久生情,把自己的情感投射进研究对象。尽管历史讲究的是客观冷静,但历史家也是人,不可能免除七情六欲,历史家的这种情感当属人情之常。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不少历史家是以人物为研究对象的,比如人们比较熟悉的陈铁健先生之于瞿秋白、杨天石先生之于蒋介石。其中,唐宝林先生尤其突出,迄今为止,他几十年的学术生命都与陈独秀相伴。他自己在不久前出版的《陈独秀全传》中写道:“我因十年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陈独秀冤案‘正名’平反工作,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极多的感情,替陈打抱不平,因此对他自身的弱点探讨甚少。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难以自拔。”  唐先生很坦诚,直率地谈到了他的这个“弱点”,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未必是什么弱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道尽了多少写作者的一腔情怀,揣摩起来,这也未始不是唐先生这本洋洋百万言的大作的写照。 唐先生这一代,基本是和1980年代前后开始的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同时成长起来。对于近代史学界而言,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又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标的。陈独秀从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中国革命的叛徒慢慢还原为新文化运动领袖、启蒙思想家、革命家。在这样的还原历史的进程中,唐先生是见证者,也是陈独秀真实历史形象筚路蓝缕的亲身构建者。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大概很难体会这一代历史学者的承担。剥离那些多年构建,尤其被“文革”推向极端的叙述体系,不仅要付出学术上的辛勤努力,还要顶着政治上有形无形的各种压力。历史是个很有趣味的学科,人人都似乎懂得一点历史,但大众传播的历史常常却是怪力乱神。近代史尤其中共党史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敏感,使掌握历史事实的这些少数历史家,传播真相、说服大众的过程,不得不面对误解、讥嘲甚至政治批评。因此,在他们前行的道路上,或多或少还带有某种为寻求真相而牺牲的道德上的悲壮。 如果理解了这种背景,前面唐先生提到的投入感情,打抱不平,就变得更好理解。在拨乱反正的时代,在不断撕裂习见陈说时,有时的确需要历史家的担当和勇气,需要择善固执的坚持。唐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陈独秀这个领域里耕耘,当然不会不受到陈独秀自由、民主,追求真理的气质感召,所以,唐先生直言:“应该承认,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这样的判断,即便其中某些说法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但出自一个多年浸润其中的优秀研究者之口,还是不能不认真对待。有人说,做人物研究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样的原则,说来容易,做起来何其之难。入乎其内这一点,唐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特殊境遇,他的体会应该尤为深刻。读唐先生的《陈独秀全传》,处处可以感到传主和撰著者的精神交相融合、浑然一体,可谓证明历史家之爱的生动标本。 出乎其外,自然也是唐先生努力的方向。他在前言中提到,为摆脱成为传主辩护者的嫌疑,他特地在内地版本中补写了一节“陈独秀自身的弱点”,探讨大革命失败中陈的责任问题。自然,这样的努力不会仅仅体现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对陈独秀早年成长经历的描述,还是对其成为革命领袖后功过的评断,《陈独秀全传》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恰恰在读到唐先生增补的这一节时,作为读者,倒是稍许感到一点不满足。这一节中有一个重要论断:“说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同时,也应说明,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能识别、不能抵制这条错误路线的问题。” 其实,这个论断中的某些话语,熟悉中共党史叙述的读者应该不会陌生,比如右倾机会主义,当年就是戴在陈独秀头上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对陈独秀使用这样的概念。不过,当它被使用在共产国际的头上时,多少又让人感觉到了历史诡异的轮回。 说到大革命的失败,几年前,笔者曾经写到:在海峡两岸的史书中,1924-1927年的这一革命分别有不同的指称,大陆史书一般多称大革命,台湾方面则多称国民革命。不同的称呼,隐含着对这场革命不同的目标取向。相对于国民革命,大革命更强调革命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要求革命可以满足中共所期望的工农等普罗大众的要求,正是从此一意义上,会有所谓大革命失败的叙述。而从国民党的视角看,国民革命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导致了全国性统一政权的建立,国民党开始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实践程序,当然不会被视作失败。 无论是从革命的彻底性上界定大革命的失败,还是直截了当从国民党夺取并独霸政权角度理解中共的失利,有一个背景都不能忽略:即唐先生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中共还只能做配角和助手,还不具备与国民党较量的力量,中共要在这一时期夺得政权几乎是天方夜谭。由此,隐含的逻辑就是:当掌握武力的国民党破裂国共合作,独揽中国的控制权时,中共当年事实上并没有与国民党争夺的余地。如果承认这一点,那所谓大革命失败的说法,就变得有点让人纠结,因为成功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正因此,如唐先生所说,要陈独秀为大革命失败负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问题是,陈独秀固然不能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但共产国际就可以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吗?既然中共的成功在当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又如何可以苛求共产国际和苏俄为此负责?其实,中共早期的创建、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这是我们回顾历史时无法不直接面对的,说共产国际是襁褓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保姆,并不为过。中共从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党,几年时间内,就发展到数万人,拥有全国性影响,成为中国政治中此后任何力量都无法忽略的政党,无论如何,共产国际都功不可没。当然,事后回望,这些指导有正有误,或者说本身就难言对错,但当年的决策者不可能像后人这样高屋建瓴、智珠在握,所以出现问题在所难免。当我们试图用历史的局限、实力的对比为陈独秀洗清那些泼在身上的污水时,似乎也不能顺势将之转嫁到另一个历史对象身上。尽管,历史家难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所谓爱常常自私,不过,毕竟也有另一句话:大爱无边。 唐先生是一个真性情的研究者,敢爱敢恨,他面对的陈独秀又是一个如此性格鲜明、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动的巨人,巨人蒙冤,的确让人扼腕,因此,唐先生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解读让人同情、理解和尊重。不过,很多时候,历史还会呈现许多灰色地带,历史的解读会有丰富多样的图景,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可以笼盖的。尤其像陈独秀,这样一个永远的旅人,一个思想上的开拓和漂泊者,一个中共革命的开创和脱队者,许许多多的话题还有待阐释、理解。唐先生这部书为陈独秀研究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这是唐先生努力多年的巨献,价值无待多言。不过,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个一个待解的问号仍会不断生成,此正应了一句话:生无涯、爱无尽、问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