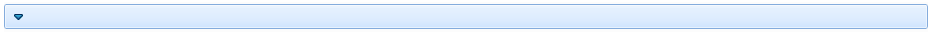注定了徒劳无功的晚年政治活动
作者:冰云
对于声名显赫的陈独秀来说,出狱后的他原本有好几条生活路子可以任意挑选,(1)而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能保证他晚年过上颇为稳定、舒适的生活。但是,陈独秀却回绝了好友们为他谋求生活出路的好意,自然更拒绝了政敌拉拢自己的优待安排——他对自己政治上的何去何从已经有了明确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算。陈独秀在在南京居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奔向逐渐成为抗战大本营的武汉——他仍旧雄心勃勃地企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刚刚出狱时,陈独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托派领导人让他回上海重整旗鼓的建议。重新焕发起政治热情的陈独秀不再刻意掩饰他与中国托派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和冲突。中国托派——这个在他眼里基本上将抗战局限于亭子间热烈的文字争吵的派别——让陈独秀深恶痛绝,更何况晚年的他在托派内部已经微乎其微的影响力根本无法触动这群从不缺乏革命激情的教条主义者僵化的思维。因此,陈独秀不再像以往那样,用心良苦地淡化、弥合彼此之间关于理论问题的争端和裂痕,而是撇开托派组织,试图以个人的身份和力量开创崭新的政治局面。
1937年9月9日,陈独秀乘船离开南京,于14日抵达武汉。刚到武汉,他租定武昌城里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暂住。(2)不久后,又搬到一位姓兰的家里居住,“这位姓兰的慕陈独秀的名,特地请他去住,房子很像样子,有家俱。” (3)据王文元先生回忆:陈独秀“那时住的是一所颇具庭园风味的旧式平屋。……独秀只付点象征房租。老人其时身体很好,起身早,在监狱里养成了来往踱步习惯,他出来后仍旧坚持着,每早晨就在屋前荒芜的园子里遛步。” (4)可以看出,在这段时间里,陈独秀的精神是愉悦的,物质生活方面与以往相比,也是颇为宽松的。
坦率地讲,出狱后的陈独秀在群雄逐鹿的政治舞台上已经基本上沦落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局外人,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但是,在刚刚踏出铁牢的时候,陈独秀更愿意把走出铁牢当作实现自己未泯灭的政治抱负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但是,陈独秀之所以在政治舞台上顽强地表现自己,与其说是出于对参与政治的本能的热心,毋宁说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炽热的爱。陈独秀可以经受住高官利禄的诱惑,可以放弃对多少人趋之若鹜的权力的角逐,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面对沦落的山河而心如止水、无动于衷——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人间炼狱图是萦绕在陈独秀心头的久久挥之不去的揪心的阴影。因此,挣脱了铁牢束缚的他焦躁地参加进了全民同仇敌忾的抗日协奏曲中。宣传抗战就成为他最愿意为之尽心尽力的事业。
仅仅从陈独秀在短短的时间里发表的为数不少的演讲和文章来看,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参与抗战非同寻常的激情。在武汉的一段时间里,陈独秀宣传抗战的文章和演讲主要有:《抗日战争之意义》、《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打倒消极先生》、《“言和即为汉奸”》、《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为自由而战》、《抗战中的党派问题》、《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怎样才能发动民众》、《抗战中应有的纲领》、《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我们断然有救》、《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等等。可以说,宣传抗战时期的陈独秀是他文字生涯的另一个高产期,这不仅是从他撰写的文字的数量上说的,而且是从文章的质量方面来衡量的。陈独秀在这段时期的文字,完全可以与他在新文化启蒙运动时期撰写的那些摧枯拉朽的战斗性文字相媲美。
从当时的报纸记载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来看,陈独秀的演讲还是很受欢迎的,与上层政治人物将陈独秀当作碍手碍脚的“多余人”的微妙情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陈独秀在普通民众中仍旧保持着一副博学、和蔼、品质高尚的“大人物”的正面形象。尤其是在那些青年学子当中,他们不但愿意一睹一代巨子陈独秀的风采,更愿意将他的言论当作一位智慧的长者淳淳的教导而铭记于心,对他也并不存在政治上的偏见和防范。(5)
1937年12月,出狱后的托派领袖王文元先生也到了武汉,多年的分别使得两位老朋友的聚面相当亲切、融洽,但是,当谈到实际政治问题后,王文元先生发现,经过多年的监牢生活和潜心思考,陈独秀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位昔日的托派领袖 “非常不满意上海的托派组织,”(6)他毫无掩饰地向王文元先生发泄着自己对这个组织的严厉批评:上海的托派组织的作风“就是继续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7)王文元先生钦佩陈独秀永远不失其锐利的政治眼光,但对他的许多政治策略却根本无法苟同。
监牢中数载的囚禁和潜心思索不仅让出狱后的陈独秀与中国托派分道扬镳,他与国内的其它政治派别也丧失了融入到一个组织里的共同语言。这个孤独又倔犟的老斗士越来越不习惯让自己独行特立的政治声音被其他党派整齐嘹亮的大合唱所淹没。
在武汉,陈独秀除了卖力地写文章、作演讲宣传全民抗战之外,再就是满怀信心地开始实践自己思考了很久的政治主张——联合一批“不拥国,不阿共”的民主势力,企图在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开创出与国共争雄的局面。
陈独秀认为:“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纲领去团结反国而不阿共的政治派别,另一方面则积极地跑进抗日的队伍去,为未来的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8)王凡西先生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了陈独秀颇具实干精神的政治活动:
独秀的工作态度当然不会限于空谈。凭了他的地位和关系,很快便开始了具体的接触。原属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百二十旅,“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在该地驻防,直接与日本军开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旅长何基沣,其时已被翟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这个军人很不平常。据独秀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我以独秀的关系与他见面时,他的创伤已愈,不久便要回到部队去,相谈之下,他予我的印象不坏。他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他深深地懂得一点: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养伤期间,他几乎读遍了汉口能买到的有关乎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和思考的结果,他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队里,为士兵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在这样的探索中,他与独秀发生了关系。他们二人很谈得来,这军人对独秀执礼甚恭,待如师长。……在有我参加的几次谈话中,涉及的均是关于今后政治的方向问题。一个中心思想被确定下来,就是: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9)
……
与军事图谋并进的,独秀正与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另一部分“民主人士”(我已不记得究竟是哪些人)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的目标。这个酝酿在当时武汉是相当有利的。国民党的统治委实太不得民心了,以至不但工农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就是从来用户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怨懑不平,日益采取了反对派态度。……陈独秀此时以他特殊敏锐的政治嗅觉,确认我们(他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托派自居的)必须参加此一运动,借以扩大我们的影响;打破我们自建的与人筑的围墙,且使这个普遍而真实的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不为斯大林党利用了去。(10)
陈独秀的政治活动在当时就引起了托派成员中那些赞赏他的政治眼光和魄力的王文元、濮清泉等人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为军事实力做姨太太的工作很有可能得不偿失,让自己的组织遭到军事实力的叛卖和屠杀,国民革命中的教训太深刻、太触目惊心了,他们担忧自己会会重蹈中共在国民革命中惨遭叛卖和杀戮的覆辙。但陈独秀显然不以王文元等人的意见为然,他说道:
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有过以前和军人打交道的经验,今后我们应该很清楚地懂得,我们在现存军队中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最后,我认为何基沣本人不是冯玉祥式的狡猾之徒,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力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表明了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受到任何损害。(11)
陈独秀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表露了这位不气馁的老斗士渴望重新有所作为的雄心和魄力。但是,残酷的政治环境让他收获的只能是命中注定的失败和屡屡打击的苦果——命运之神对陈独秀绝不会那么慷慨和公正,它不会将幸运的曙光再次洒照在这位昔日弄潮儿的身上。
托派成员的担忧是建立在与军事力量的合作实现之后出现的恶果,但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却使得这种恶果根本不会出现,因为陈独秀的政治意图仅仅在设计之初,还没有发展到重蹈国民革命时期覆辙的时候,就被粗暴地扼杀了:王文元、濮清泉和“另外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也是同志),将于二三日内随何基沣回到内河的师部去”,王文元“算是秘书长,小濮仿佛是参谋(已记不真了)。平汉路车的票子都已到手,可是临动身的前夜,突然接到了通知,何基沣被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12)
与此同时,一场声势颇为壮大的“汉奸风波”彻底将陈独秀摒弃出了政治舞台。
作为共产国际使者的王明在刚刚回国不久就以一系列大动作企图将中国托派和陈独秀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他先是在中共内部会议上声色俱厉地“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和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13)接着又在1937年12月4日的《解放》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说污蔑似乎更加准确)中国托派的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文章写道:在抗战开始的条件下,“日寇侦探机关,必然更加设想安插自己的侦探、奸细、破坏者、暗杀凶手和暗害者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首先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他还煞有介事地说,托匪分子按日寇侦探机关的指令,在上海、南京、西安及其它地方进行破坏和侦探工作。还说薛农山、任卓宣和郑学稼是托派。黄平、徐继烈、屠庆祺(杜畏之)等,每月从日寇“华北特务机关”,“领取五万元的津贴。”(14)
而康生在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报(第一卷第29、30期)上发表的一篇16000余字的长文-——《铲除日寇汉奸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对“汉奸风波”的引人注目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篇文章杀气腾腾地向世人昭示着陈独秀等托派的罄竹难书的累累罪状。似乎他想用自己惊世骇俗的文字为中国托派奏响让他们狼狈地爬回历史坟墓的挽歌: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成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日本津贴有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15)
指鹿为马的卑劣政治诬陷犹如一枚重磅炸弹丢进了本来就暗流涌动的中国政治界。
尽管社会上那些对陈独秀怀有好感,并且了解他出狱后所作所为的人们,如周佛海、王星拱、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等人挺身而出,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为他辩护,陈独秀也愤恨难平地在3月18日致信《新华日报》为自己辨白,但是,“汉奸风波”将陈独秀赶出政治舞台的效果却也是立竿见影的。
在中共粗暴地污蔑陈独秀为“汉奸”的时候,那些陈独秀曾试图团结起来的“民主人士”虽然对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大多是嗤之以鼻、不以为然。但从政多年的敏感却让他们觉察并读懂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背后的内涵——以及国共两党对陈独秀重返政治舞台的畏惧和嫉恨。“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在当时和陈独秀谈起此事时就含蓄地指出了对陈独秀的污蔑是“政治问题”。因此,民主人士都开始自觉或被迫地疏远了陈独秀——尽管并不是像躲避某种病菌那样完全切断了彼此之间的一切关系。
毫无疑问,横生枝节的“汉奸风波”让中共的政治声誉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这件不得人心的风浪也让中共(当然也包括国民党)实现了一个难以明言的政治目标:它彻底摧毁了陈独秀重返政治角斗场的意志,为国共两党除去了隐隐作痛的一块心病。
自然,陈独秀的失败也因为他企图将民主派别团结成钢板一块的有实力的政治团体的愿望只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中国的民主派别自身有无法克服的弊端,彼此勾心斗角的浓厚教派意识的束缚和他们对个人独立见解过于矜持的坚持在政治上总是不合时宜的,从而分散了他们协调一致的凝聚力。这些弊病在国共两党空前强大地霸据政坛的局面前面使得他们的政治抉择只能是毫无前景可言的死胡同。
就这样,陈独秀满怀信心的政治努力在国共两党的夹击下全都成了泡影。
晚年的陈独秀忍受着黯淡而坎坷的生活的折磨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言论睿智高远也好,他的行为倜傥卓异也罢,他可以一次次地在中国政坛引起动荡,他甚至能够成为全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新闻焦点人物,但他永远也不可能再成为掌握时代巨舰航向的革命舵手。他在政治舞台的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像推着石头上山的弗弗西斯那样,竭尽全力却总是徒劳无功。这样的结果并不是说陈独秀的才干不足以承担历史的重托,而是历史不可能再给他提供一种契机让他以时代舵手的身份重新跨进政治洪流的风口浪尖。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拿破仑一旦以拯救社会秩序的‘利剑’角色出场,便以此排除了所有其它将军扮演这一角色的可能,尽管在这些将军当中有些人扮演这一角色也并会和他一样和相差无几。” (16)当时中国政治界,只有手握重兵的实力派才有做“中国的拿破仑”的资格。而陈独秀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但是,陈独秀的政治计划的夭折并不简单是出于利用军事势力的落空,陈独秀政治上的难以有所作为源于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和现实中的国共两党的空前强大: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而专制毒素又弥漫整个社会的国家里,“在实践上成功的中国政治领袖不是靠演说,靠文章,靠选票,而是靠实力,权术,政治上的‘得人心’,组织上的‘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 (17)中国几千年来在政治角斗场上比拼的政治人物无一不是手握重兵,靠权术招兵买马,靠武力降服对手,秦皇汉武如此,唐宗宋祖如此,“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更是如此。而陈独秀不仅“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他那我行我素、口无遮拦的爱发议论的态度实在是让许多政治领袖无法接受的聒噪。他肆无忌惮地指摘其他政治势力的各种缺陷时,也就是给自己的政治生涯挖掘坟墓),陈独秀“更缺乏有人身依附特性的实力基础(如军队、干部)。” (18)而这一点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任何雄心勃勃、才干卓越的人也都已经无力打破的局面。
因为经过二十年代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的冲击,国共两党都不失时机地崛起壮大,并且以其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各自获得了广泛的信仰者和追随者。从此,中国现代史上双雄并立的局面即已形成,其他政治派别已经丧失了任何独树一帜、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机会,更何况国共两党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会对自己一统天下构成威胁的其它政治派别的崛起而无动于衷。对第三势力的发展进行毫不留情、不择手段的排斥和打击或许是这对都以革命政党相标榜的政党唯一相同的政治见解。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曾经数次出现过某些政治势力积蓄实力,想要独树一帜,从而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治尝试,但这些努力最终都无一例外的胎死腹中或是短期后就销声匿迹。
国共两党之所以能保持长久的对峙局面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都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迥然不同的特殊政治派别——它们的背后都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他们实现政治愿望的利剑。任何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第三势力,等待他的只能是被枪杆子敲碎头颅的厄运。(值得注意的是,发展自上而下的严密政治组织和组建强大的无条件服从党的军队,这两点国共两党都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谁的枪杆子厉害,谁就能够在中国毫无阻滞、并且名正言顺地推行它的政治主张,这就是现代中国(实质上这是中国保持了几千年的现实)所面对的惨酷而可悲的现实。至于人民,他们总是从驾役并利用他们的政治势力那里得到崇高而又廉价的赞美,但实质上麻木又闭塞的人民根本无力影响残酷的、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过程,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承担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政治斗争的结果。
如果说刚刚跨出监狱铁门的陈独秀还没有认清自己“多余人”的尴尬地位,还企图凭借一腔热血,一身本领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到了他漂泊四川,生活困顿时,他已经彻底承认并接受了这一冷酷的事实。进一步推理,如果“汉奸风波”(这场风波自然是蓄意的政治阴谋)没有阻挠住陈独秀团结“不拥国,不阿共”的民主势力的政治活动的话,那么,陈独秀晚年的生活境遇或许会比漂泊入蜀还要凄凉困顿——他在政治洪流的搏击中付出的很有可能是生命的代价。从许多企图凭借积蓄独立的军事力量而在国共两党之外独树一帜的政治人物的悲惨下场中,我们完全能够预测出陈独秀如果选择与他们相同的路子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注释:
(1)据包惠僧先生回忆:陈独秀出狱后,“有一家美国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不去……他说他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当时,胡适、张柏龄、周佛海等想拉陈独秀进国防参议会,他不去。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第303—30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蒋介石甚至还有让陈独秀出任“劳工部长”的意思,并愿意为他提供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让他再组织一个共产党,陈独秀对此同样予以拒绝。
(2)陈独秀致耕野(即陈独秀老友汪孟邹——引者注)信,《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376页;
(3)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第305页;
(4)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21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5)见许俊基:《许俊千面邀陈独秀作抗日演讲的回忆》,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1—39期合订本,第438—440页;
虽然有一些接近中共的学生对陈独秀这个托派领袖抱着某种成见,但他们似乎并没有从陈独秀的演讲中嗅出值得戒备的“托派”气息,也就没有作出什么过激的行为。见苏雪林:《我认识陈独秀的前前后后》,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二辑,第325—32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213页;
(7)同上书,第216页;
(8)同上书,第216页;
(9)同上书,第219页;
(10)同上书,第222页;
(11)同上书,第220页;
(12)同上书,第221页;
(1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22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14)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解放》第26期;
(15)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周报(1938年1月28日、2月8日);
(16)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转引自《流亡的先知》,[波兰]伊萨克·多伊彻著,第26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7)李泽厚:《胡适 陈独秀 鲁迅》,《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04页,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