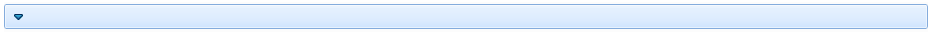先父梁漱溟入北京大学任教,始于1917年秋冬间;辞去教职离开北大则在 1924年夏,前后约七年。这七年的北大生活,在他一生中的意义非同一般。
一
早在1912年先父就曾见过蔡元培先生,且不止一次。那时蔡先生是内阁阁员,任教育总长。先父那年十九岁,任《
民国报》记者,常出入国会、国务院,在公众场合见过蔡先生;景仰蔡先生,却无单独面谈的机会。1916年秋冬,又去见蔡先生。这次去与四年前不同,不是去采访,而是以自己刚写成发表的长文《究元决疑论》向蔡先生请教。
先父离开《民国报》之后,居家闭户不出,潜心研读佛家典籍,前后约四年。后来先父即将几年来的研读心得加以总结,写成了《究元决疑论》,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惟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先父早在中学时就读过蔡先生翻译的《哲学要领》一书,也知道蔡先生喜爱哲学。1916年下半年,先父得知蔡先生自欧洲回国,已来京出任北大校长,即请范源廉先生代为先容,征得同意后,即往谒蔡先生。据先父回忆:“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后来“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大家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末后的几句话真正的打动了他。常言道教学相长,抱这种态度来北大任教再好不过。自己怎能舍弃这样好的学习机会呢。于是先父将此事应承下来。不过当时先父正在司法部工作,为司法总长张耀曾他的舅父任秘书,一时不得分身,实际到校任职,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1917年10月末或稍后些的一天,先父终于到校任职。这一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晋见蔡先生,其经过他有以下的记述:
我的意思是,不到大学则已,如果到大学作学术方面的事情,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员便了,一定要对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所以我第一日到大学,就问蔡先生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先生沉吟的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我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而我这种发挥是经过斟酌解决的,非盲目的。
人们不应忽略,当时的蔡先生已年届半百,是清末的翰林,又曾游学欧洲,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老前辈。而先父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不过中学学历,只对佛学有所钻研,刚受聘为讲师,且尚不曾一次登上讲台。由此可见,先父似过于认真,又颇为自信;认真与自信得似乎在老前辈面前有欠谦恭,而蔡先生反显得十分宽容大度了。
先父入北大经过,大体如上所说。可是或出于对蔡先生求才不拘一格表示推崇,或为了对先父自学成材表示赞许,不时有种种传言见于书刊。如说,先父考北大不被录取,于是发奋自学,终于实现了“不录取我当学生,我却要去北大当老师”的愿望。又如说,蔡先生求才若渴,虽知先父曾未被北大录取,但仍坚持“当学生不够格,那就请他来北大当教授吧。”实事上先父中学毕业后即参加革命活动,不谋就业或升学,从未投考任何大学。先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作过更正说:“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但似效果不大。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
二
先父不曾入过大学之门,却能登上大学讲台,自然有些不同寻常。据《北京大学日刊》上的一则二三十字的简短“通知”,可以确知他首次开始授课的日期为1917年12月5日。他七年的教师生活就从这天开始了。
七年间他所讲授的课程大约有三门:“印度哲学”、“唯识学”与“孔家思想史”。“印度哲学”大约每学年均为高年级学生讲授一次。“唯识学”自1919下半年起,约讲了两年,即改由熊十力先生担任。“孔家思想史”则讲授于离校前最后一学年。这门课颇受人们注意,除了注册选修此课程者外,自由来听讲的学生亦很多,还有来自校外的。据先父记忆:“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可见“来听者之多”;可“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
于授课之外,先父七年间所作讲演不少,如“佛教哲学”(1918上半年)、“孔子哲学”(1918下半年)、“因明学在佛法中的地位”(1919年)、“宗教问题”,以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其中以末一个最为重要。
东西文化问题的这一讲演作于1920年下半年,而对于此问题的思考与酝酿则早在入北大之初(1917)。先父说过“我当初研究这个问题是在民国六七年的时候”。到了1920年下半年,他终于将自己对此问题三四年来的思考与研究所得,在校内作了连续讲演,约一二十次之多。
这一讲演的进行似也有些不同寻常。在开始之前,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一则启事,其内容是说他“决定在讲印度哲学、唯识哲学之前,先取东西文化问题略为剖释”,为此“拟以印度哲学之三小时略讲东西文化,其唯识哲学两小时暂不上课。一俟讲毕,仍各照课程表办理”。这就是说,原来由他讲授的两门功课全暂停,改为每周用三小时介绍个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结果。原有课程暂停多久,可视需要而定,并无限止。有位老北大人的回忆录中说:“开什么课是教师的自由,至于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先父当年似即曾享有了这种“自由”。
另有一位老北大名田炯锦(1919年入学),在他的回忆文字里说及自己对教师授课的印象。关于先父他是这样写的:“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各课,有甚多创见,尤其讲儒家的所谓‘仁’,我最佩服其见解正确。但他不甚长于言辞表达,文字亦欠流畅,每当讲解道理时,不能即行说明,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深思。”台湾《传记文学》,1973年第1期此处“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把一个人冥思苦想的样子,不是刻画得有几分传神吗?由此想到,教师讲课,如果不人云亦云,或不照本宣科,而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那是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的。
先父常说,思考问题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可是这也往往为他带来了苦恼——失眠的痛苦。他譬喻自己的思想活动好似根很长的绳子,时常放出去就难收回来。先父除了幼年孱弱多病,一生甚少病痛之苦,只是不时地要与失眠作斗争。1919年暑期,他为了加紧备课,就又严重地失眠了。“去年暑假急急忙忙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了两章,乃开学增唯识哲学一科目,又不得不编写《唯识述义》,想着兼程并进,竟不成功,反弄得夜不能寐的症候,请了一个月的假,到现在三个月没好,还须觅地养息。”这是事后他写下的一段话。在北大期间,因严重失眠,他至少有两次写信给蔡先生,请求准予他辞去教职,均为先生挽留,而建议他可请长假休养。这是蔡先生对人才的关爱,当然也就是对先父的关爱。先父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曾写下这样的话:“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其原因就是“蔡先生具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纪念蔡元培先生》)
三
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以后,多方网罗人才,许多专家学者先后来到北大,真可谓人才荟萃。旧派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季刚、陈汉章诸先生;新派学者首推陈独秀、胡适之,以及李大钊、周树人、顾孟余、陶孟和等各位,当时都先后汇聚于北大。领导新思潮的《新青年》也随陈独秀先生至北大,由上海迁北京出版,于是北京大学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发祥地与中心了。先父正是在这一时期走入北大。先父尝回忆自己亲历这一运动,当他入校时,“这恰值新思潮(‘五四’运动)发动前夕。当时新思潮既倡导西欧近代思潮(科学与民主),又同时引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我自己虽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环境气氛却对我这讲东方古哲指释迦与孔子——笔者之学的无形有很大压力”。当年他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似不难想象。这种压力既激励了他,又磨练了他。显然这激励与磨练与他日后的成就不无关系。而先父能有这样机遇,又不能不说是出于蔡先生了。当年北大学生出版一种杂志《新潮》,还有一种叫《国故》,隐然代表了新旧两派。先父说:“我个人虽偶尔投书于《新青年》或《新潮》却不属新派,亦非旧派”。他是很看不起那时的旧派的。他曾说:“那《国故》只堆积一些陈旧骨董而已,”而“那些死板板烂货也配和人家对垒吗?”既然“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我自无从表示赞成”。而由于旧派如此无能,以至于“现在谈及中国旧化便羞于出口,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先父如此认识旧派,不同意旧派之所为,他不愿与旧派为伍是很确定的了。
现在要问:他是怎样看新派的呢?这不难从他对新派的代表人物的态度及评价中看出。
先说陈独秀先生。先父对陈先生等提出的中国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主张,是完全赞同的。他当年即这样写道:“其实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批评无条件地承认”,“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对陈独秀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贡献,他也曾这样讲过:“我常说中国讲维新讲西学几十年;乃至革命共和,其实都是些不中不西的人,说许多不中不西的话,做许多不中不西的事。他们只有枝枝节节的西方化零零碎碎的西方东西,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看通窍,领会到那一贯的精神。只有近年《新青年》一班人才算主张到家”。而在《新青年》一班人中的灵魂人物“陈独秀先生是攻击旧文化的领袖;他的文章有好多人大怒大骂,有些人写信和他争论。但怒骂的止于怒骂,争论的止于争论,他们只是心理有一种反感而不服,并没有一种很高兴去倡导旧化的积极冲动,尤其是他们自己思想的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样禁得起陈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而陈先生自然就横扫直摧,所向无敌了。”
以上这些称赞陈先生的话,都是先父当年所写。就是离开北大数十年之后,回顾往事时,他对陈先生仍称道不已,认为他“是反封建的一位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又说当年的陈先生“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波澜!”
先父对于胡适之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这是开创性的”。而“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这对提倡用白话文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
由于思想见解终归有不同之处,当年先父与陈、胡二位之间思想交锋自是常事,于是以什么态度展开讨论与辩难也就成为须要辨明的问题。对此,先父发表了自己看法。事情是由胡先生题为《一年半的回顾》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文中说《努力》杂志一年多来的许多文章都不及“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先生则为文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的一线曙光!”先父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这令我很难过”。
在感叹之余,先父表明说“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在这一点上,彼此是“有同的一面”,即大家都是愿为社会进步尽力的。他又说:“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这就是先父对新文化运动中新派的根本态度。
同时,先父又承认:“我们的确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大家“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我并不要打倒胡适之、陈独秀而后我才得成功。”
这种态度简要地说,或可用四个字概括:“和而不同”。这与蔡先生所倡导并实行的“兼容并包”在精神上也是相通的吧。
四
东西文化问题可算是先父在北大七年间所从事的最为有意义的一项研究,他为此付出的时间与心血是最多的,所取得的结果也最为重要。
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先父曾说:“我当初研究这个问题是在民国六七年的时候”,这就是说刚入北大的头两年(1917、1918),他就开始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了。可那时他“很苦于没有人将东西文化并提着说”,或者人们口头上或笔墨上虽说什么“东西文化”这名词,且说得很滥,可是“大家实在不晓得东西文化是何物,仅仅顺口说去罢了”。
1920年将放暑假前,北大教职员开会,欢送蔡先生与几位教授赴欧美考察教育。先父也参加了这欢送会,事后他写下了以下一段文字:
我记得有几位演说,他们所说的话大半都带一点希望这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的意思。我当时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的人却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陶孟和先生同胡适之先生笑着对我说:“你所提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
事后先父感慨地说:“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在先父看来,当时的旧派只是“能感觉西方化的压迫而表示反对的”,但只是“为东方化盲目的积极发挥”而已,“他们并非能看到东西文化问题,而去作解答”。至于新派,“是被世界西方化的潮流所鼓动”,只是“能感觉西方化的美点而力谋推行”,“有似受了药力的兴奋,也并非看到这东西文化的问题,有一番解决而后出之”。
上述这种情况,在先父看来是表明人们对此问题的解决的急迫性缺乏认识。他说:“这个问题自是世界问题”,“而直逼得刀临头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身丧命倾的却独在中国人,因为现在并不是东西文化对垒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化存亡的问题”。所谓东方化的存亡,自是包括中国文化的存亡,也就是中国民族是存是亡的问题。“这种险恶的形势想要模模糊糊混过去,是断乎不行的,乃不料逼到眼前的难关,大家竟自无人看见”。
上面这几句话是先父1919年暑期所写。这就是他眼中当年东西文化问题的实况。此时在他来说,思考并研究此问题已有两年之久,而且获得了一个初步结果。转过年来,即1920年秋冬间,他即首次以连续讲演形式,在北大报告了自己关于此问题的研究结果。再过一年,即1921年,他应邀去山东济南再次就此问题作了连续讲演。同年,将两次讲演记录加以合并整理,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首次出版了。
此书的结论是,全世界的文化可大略分为三大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它们各自有其“特异色彩”与“根本精神”。它们之间虽有不同,但非古今新旧之分。总之,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各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依此观点,一如现代西方文化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同样具有它不可磨灭的意义与价值,并将在今后为人类生活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这种看法,在当时“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高涨声中,无疑是在维护并赞叹孔子,这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应。主张“全盘西化”者,认为这是对新思潮的一种反动,自然是反对;而对那些对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的人来说,则使他们恢复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而表示赞同。但无论是褒是贬,先父自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著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有在这里著书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要说的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至于后人评说,以为此书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作之一,他本人并因此书而被视为儒学的先驱,这些自然都是他始料所不及之事了。
五
先父在北大任教六七年间结识的朋友为数不少,如梁启超、林宰平、伍观淇、熊十力、李济深、陈铭枢、李大钊诸先生。他们中多数人比先父大十岁或二十岁,因此可算是忘年交。先父认为彼此关系在师友之间。现在只举两位先生说一说。
先父曾说:“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先父早年致胡适之先生的信里曾说:“类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亦为先生所知道的”。在这里所说“独与守常相好”,自然是表明先父与李大钊先生关系不同一般。
先父入北大后,不久李大钊先生也任教于北大,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二人同在一所学校,而图书馆又是先父常去逗留之地,更何况早在进入北大之前,二人即已相识了,十分熟识自不待言。先父曾回忆说:“当我每次到北大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之后,必定去图书馆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也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二人如此交往,可见彼此相交之深,毫无客套。
197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送来一张四人合影旧照。先父审视良久,便写下这样几句话:“我与守常既而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息”,因此有此“我与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我四人在中央公园的相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五十年以上,展示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张申府与雷国能二位本是先父在顺天中学堂同学,又均与李大钊先生相识。)
1921年末,先父决定放弃出家的心愿,将要成婚,特意为此“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李先生则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的事了”。先父还记得,李先生曾解释说,他父母早逝,自幼随祖父母生活,而二位老人自顾年迈,故早早为其完婚;当时李先生似仅十二岁。
先父离开北大三年后(1927年),李大钊先生为军阀张作霖杀害,为革命献身了。当时先父尚在北京,虽曾参与遗体装殓事,但仍感“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又数年后,先父在致胡适之先生信中,谈到“我们怎样解决中国问题”时说:“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个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般不行,却亦肯想这问题”,“然我则没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条路的决心与信力,更没有拦阻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了”。可见在先生已牺牲多年之后,对先生崇敬之情仍萦回于怀。
还应说到先父在北大时期结识的另一位朋友熊十力先生。
1919年上半年的一天,先父收到一张寄自天津的明信片,寄信人名熊升恒,南开中学教师,素不相识。明信片上所写的话不多,大意是说:在你写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中骂我的话,我看到了,你说的不错。希望有机会见面晤谈。不久,学校放暑假,熊先生即来京相会,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毕生的朋友。
先父之所以责备熊先生,是因为他在《庸言》(梁启超先生主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到佛家,说“佛道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其害不可胜言”。先父即在《究元决疑论》一文中指名道姓批评了熊先生,说“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二人分歧起自佛学,二人一见面,谈话仍从佛学问题入手,最后归结是先父劝熊先生研究佛学。
1920年,先父介绍熊先生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事佛学研究。1922年,先父在担任“唯识学”课约两年之后,“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遂建议另请高明,得蔡先生同意后,遂将熊先生介绍来北大,接替他讲授“唯识学”一课。
熊十力先生原名“升恒”,字“子贞”,长于先父八岁,湖北黄冈人:未曾受过正规教育,只在乡塾里读过几年四书五经;有时边放牛,边自学,终成为著名哲学家。与先父具有中学学历相比较,那熊先生才更是位自学成材的人物了。后来熊先生转而研究儒学,卓有成就,终被认为是“新儒学哲学的奠基人”。
先父在北大任教七年间,又结识了一些与自己年龄不相上下的朋友,他们多是北大的学生。先父入北大时二十四岁,听他授课的同学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年纪。如冯友兰先生与朱谦之先生均只比他小两岁。又如陈政先生(仲瑜)仅小于先父一岁。结识的学生不限于哲学系,也有其他学系的,如中文系的罗常培(莘田)先生(著名语言学家),和罗庸先生(曾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也有外校的,如高师的徐铭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还有旁听生,如王恩洋等。其中陈亚三、黄庆(艮庸)、王平叔(维彻)、张俶知诸先生,后来成为先父办学或从事乡村工作的得力助手,“关系甚深,踪迹至密,几于毕生相依者”。
现存1921年9月先父与三位同学的合影一张,他为此合影曾写下这样的话:
这是我同我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麐、朱谦之、黄庆的照相,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对是第一乐事。
由以上所记,可见先父当年在北大时,他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可谓是谊兼师友。
六
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辞整理成书既已出版之后,他随即在此书自序中写下这样一些话:“我从二十岁以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万牛莫挽,但现在则已变。这个变是今年三四月间的事,我从那时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因此可以说“现在这本书是我改变态度的宣言”。这表明随着东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完成,指导他自己的人生思想也随之有了改变。这是入北大后第五年的事。
依先父的见解,人们的人生态度即人生观大略可分为三种:一是“逐求”的人生态度。即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欲望的满足就是最大幸福。能彻底发挥此种思想的为现代西方人。二是“厌离”的人生态度。以为人生是苦,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态度。发挥此种思想最到家的为佛家。三是“郑重”的人生态度。以自觉的力量郑重地去生活,而非赖外力的催逼或刺激。发挥这种思想最到家的为儒家。
先父回顾其一生,大体说去在十岁至二十岁期间,自己的人生思想与第一种人生态度相近;二十岁以后至二十八岁,其人生思想为“厌离”的人生态度;自二十八岁以后转为第三种人生态度。他晚年曾写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记述其一生的人生思想曾经历了三个时期,发生过两次转变,其中第二次转变即发生于北大任教时期,从而“归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与现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
“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如我当初见得佛家生活是对的,我即刻不食肉不娶妻,要做那样的生活,八九年来如一日。而今所见不同,生活亦改。”这又是他当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所写下的一段话。同年底,他成婚了,再过两年, 1924年先父更辞去北大教职,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在经过一些曲折之后,终于投身于农村,从事一种社会改造运动——乡村建设——去了。
先父生活在北大前后七年,对北大的种种是如此熟习,又如此亲切。这里有他首次登上大学讲台的那间教室。这里有他出入其间无数次的红楼,还有时常去光顾的图书馆。在这里,有与他曾朝夕相处、彼此辩难的同事。在这里,有与他曾相聚于课堂、相互切磋的同学。可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告别了曾培育了自己的北大。多年后他写下了这样两句话:“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