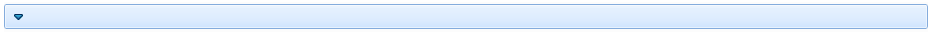|
俄國在中國現代性建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遠不限於給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提供了豐厚的資源,更重要的是給中華民族建構獨立的民族國家輸入了指導思想:這便是經由列寧主義仲介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運用這種馬克思主義分析社會問題和文學問題的方法!
說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問題,據丁守和先生考證,二十世紀初梁啟超已經在《新民叢報》上介紹過馬克思,不久《譯書彙編》、《中國日報》、《國民日報》和《東方雜誌》等近二十種重要報刊譯介馬克思理論,尤其是梁啟超和馬君武等人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階級鬥爭論、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理想等譯介貢獻更為顯著1。問題是,這些直接來自西文的譯介並沒有產生社會性效應,作為有社會影響力思潮的馬克思主義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而且在中國產生巨大實際意義的是俄國馬克思主義,即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前的蘇維埃國家意識形態的列寧主義,而不是來自德國的經典馬克思主義!俄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並發展為國家意識形態,這不僅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以實際行動號召世界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既體現「西方世界」的分裂,又符合中國人對西方愛憎交加的心態,還根源於更複雜的原因和過程:中國實踐馬克思主義在很長時間內不是對德國馬克思學說本身的自覺需求,而是因為馬列主義中的列寧主義在中國更具有實際指導意義和可操作性、蘇俄社會主義於中國很有親近感,而且這種情形屬於中國關心俄國政治革命並全方位認同蘇俄的自然延伸。
一
事實上,中國關注俄國社會革命遠不是從十月革命開始的。從陳獨秀的《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1917年4月)可以看出,中國知識界對俄國二月革命已經報有很高的認同性期望了。同時,李大釗據日文報紙《時事新報》所提供的資料而於1917年3月19-21、27、29日在《甲寅》上連續發文《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俄國大革命之影響》和《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陳述了俄曆1917年2月發生以共和制替代帝制之革命的情形,並仔細分析其原因包括俄國新舊思想鬥爭、虛無主義盛行、德國官僚主義之輸入、革命文學之鼓吹、農民困苦、皇帝專斷、官僚反動派之跋扈、杜馬上院右派黨復活、守舊派之反對國會、工黨之緣故、麵包之缺乏等,如論及深刻影響二月革命的俄國文學曰,「亦即革命文學也,其各種作者無不以人道主義為基礎,主張人性之自由發展、個人之社會權利,以崇奉俄國民生活之內容」。並且,李大釗還關注這次革命對世界和中國的影響,「俄人以莊嚴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間接以灌潤五國自由之胚苗,確認專制不可復活、民權不可複抑、共和不可複毀、帝政不可復興,即彼貌託共和之『官僚政治』,於今亦可不嘗試,今吾更將以俄國革命成功之影響,以原俄國共和政治之勢力,此因果之定律,報償之原則,循環往復,若茲其巧,或即異日中俄兩國邦交日篤之機緣歟」,斷言二月革命警示中國再鼓吹「官僚政治」和「賢人政治」已不合時宜,因為共和趨勢不可擋2。進而,針對十月革命俄國政權易手「激進社會黨之手」而導致俄國「悲觀」、吾幫「多竊竊焉為之抱杞憂」之勢,李大釗又寫下著名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稱「俄國今日之革命,誠與昔者法蘭西革命同為影響於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在法蘭西當日之象,何嘗不起世人之恐怖、驚駭而為之深抱悲觀。而後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於此役。惟其法人,十九世紀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會之組織等,罔不胚胎於法蘭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紀初葉以後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紀末葉至法蘭西亦未可知。今日俄國革命抱悲觀者,得毋與在法國革命之當日為法國抱悲觀者相類歟……俄羅斯革命是二十世紀初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時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質自異,故迥非可同日而語者。法人當日,故有法蘭西愛國的精神,足以維持全國之人心;俄人今日,又何嘗無俄羅斯人道的精神,內足以喚起其全國之自覺,外足以適應世界之潮流,尚無是者,則赤旗飄飄舉國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義之精神,入人之深,世無倫比。數十年來,文豪輩出,各以其人道的社會的文學,與其專擅之宗教政治制度相搏戰。迄今西伯利亞荒寒之域,累累者固皆為人道主義犧牲者之墳墓也。此而不謂之俄羅斯人之精神殆不可得。法人當日之精神,為愛國之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為愛人的精神。前者根於國家主義,後者傾於世界主義;前者恒為戰爭之泉源,後者足以為和平之曙光」3。1922年11月8日《晨報》刊文《昨天的蘇俄紀念會真熱鬧》,報導7日北京各團體三千餘人在北大集會紀念蘇俄十月革命,被公推為主席的李大釗發表演講稱,「蘇俄革命的歷史及對於世界的影響,有四種好處:無產階級專政;剝奪壓迫階級的言論出版權;紅軍;恐怖主義」。同時,在《獨秀文存》卷二之文《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1919)中有言,「英、美兩國有承認俄羅斯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消息,這事如果實行,世界大勢必有大大的變動。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作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4,《獨秀文存》卷三有文《俄國精神》稱,「黃任之先生說:中國人現在所需要的,是將俄國精神、德國科學、美國資本這三樣集中起來。我以為我們尚能將俄國精神和德國科學合二為一,就用不著美國資本了,但是中國人此時最恐怖的是俄國精神、所最冷淡的是德國科學、所最歡迎的只有美國資本」5,作者儘管在此沒有明說何謂最恐懼的「俄國精神」,實則指暴力革命。由此帶來對暴力革命的普遍認同,陳獨秀得知作為俄國溫和派的克倫斯基致電列寧說他的思想漸漸和布爾什維克接近的消息,提出「可見世界上溫和的人都要漸漸的激烈起來了,這是甚麼緣故呢?」6。更有甚者,胡愈之的《勞農俄羅斯之改造狀況》(1920)熱情洋溢地塑造了有親和力的新俄形象,包括給勞動者以言論自由、解決勞動者就業和改善就業條件問題、改革司法制度及其帶來的積極效果、改造教育狀況和衛生等方方面面7。
除了這種呼喚革命和新制度的意識形態認可之外,羅素訪華演講時大量涉及蘇俄印象記和馬克思主義論,也促成了中國對新俄的認同。羅素訪華演講是現代中國生成過程中的重要事件,上海《民國日報》1920年跟蹤報導羅素在華行程:11月9日發文《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羅素在湖南演講》稱,羅素把布林什維主義視為一種宣導平均分配和人人勞動並對生活有希望、主張國有化與和平主義、廢除重商主義等理想的宗教,因為「資本主義已到末路,世界的將來,布爾什維克正好發展,推到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總會失敗,布爾什維克可以發展」等;並用親身經歷莫斯科秩序井然的事實反駁那些關於赤俄內地毫無秩序和外人去會有生命危險的謠言、攻擊布林什維主義不實之論;還辨析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馬克思認為工商業發達,社會革命才能成功,但今日世界以美國最為發達,如此看來布林什維主義應該發生在美國。俄國工商業不發達,就不至於發生布林什維主義了。然而,美國應該發生而沒有發生,俄國不應該發生卻發生了,我想馬克思復活了也不能理解」,「我雖然相信共產主義是一種好學說,我雖信那是文化的進步,但我想必用漸進方法實行這主義,不必用強硬手段壓制他們」。11月29日刊載《布爾什維克的思想──羅素在北京女子高師學生自治會上的演講》,羅素在此稱「人們反對布林什維主義之處,正是布爾什維克最高尚最好的地方。如果布爾什維克把招人反對的最好及最高尚處著實地實行下去,確實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以為布爾什維克之所以為人所恨,招人反對者,並不是因為它的罪惡和不好之處,卻正是布爾什維克的功德極好之處。因為布爾什維克的罪惡和壞處,世上完全統有,彼的好處卻為世上所沒有……據我想來,除了共產主義之外就不能給女子以應享的權利及應得的位置了。在蘇俄男女間的關係,可以說比世界上哪國男女間的情形要好,雖然也許是俄國民族的天性如此,卻也因為布爾什維克的好處。但是除了共產主義制度,此外便沒有比這個好的經濟制度,可以使男女平權了」,「我希望世界上文明各國應當來輔助俄的好意,才能保守自古以來的文明。我更希望世上個個文明國,都應該以這種大好新主義來實地試驗」。羅素訪華演講雖不敵杜威那樣有影響力,但引發的爭論表明了其效果不可低估:胡愈之在《東方雜誌》發表《革命與自由》(1920年11月),積極為羅素的蘇俄言論辯護,贊同他遊俄歸來後在華的演講或答記者問的有關內容(俄國現行制度乃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之明證,俄國革命領袖之才智與其毅力不可蔑視;俄國單獨採用新制度,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和帝國主義反抗,其結果使俄國政府不能不用武力,而武力之結果不免喪失革命之本義,真自由真幸福反不可期矣),「俄國政治改造之成功,亦不能分為武力革命之結果。俄國文學者、哲學者,以精神的訓練砥礪其國民。殆已百年於茲,至此次革命而始食其果。俄國今日所以能有多數不慕利祿,忠於主義之共產黨,羅素之所述,亦何莫非精神薰陶之功。故俄國革命之成功,與其謂為托洛茨基和列寧之力,不若謂為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之力也。吾中國改造之方法,武力革命乎?平和的文化運動乎?在今日猶徘徊歧路,無所適從。茲得聆羅素先生之名論,知久經文化薰陶之俄國,猶且因採用武力之故,不能達改造之鵠,亦可以知所取捨矣」8。在《羅素新俄觀的反響》(《東方雜誌》1921年4月號)中稱羅素的《布林什維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和在中國發表的遊俄觀感,「對於俄國革命的英國及其內容,闡發得非常出透,凡是關心俄事的人,看了沒有不佩服的」,雖然美國有人稱羅素是共產主義者、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反對羅素的和平主義而推崇蘇俄革命和階級鬥爭。
正是十月革命和蘇俄在中國知識界的熱烈反響,使得「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這些抽象概念在中國變成了具體話語,甚至被提升為分析中國問題的方法。李大釗如是解釋十月革命曰,「俄羅斯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足於社會主義之上的革命」9,「由今以後,到處所見都是布林什維主義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林什維主義的凱歌的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0,並聲言締造這個新世界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乃是「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而階級鬥爭乃把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有機串聯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核心11,進而發現「孔子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年的緣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做中國人的『萬世師表』」,而是「因為他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按馬克思觀點「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甚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12。在長文《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1921)中,李大釗對俄國歷史進行了另一種敘述,即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1861年改革及其引發的自由主義運動和民粹主義運動、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這些「俄國革命首領對人民很抱一種熱望,把他們的希望放在農民身上,並經常注意村會(village mir即村社),一向把它當作未來的理想社會,但是運動愚鈍的農民去實行革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許多革命的領袖鄭重主張『教育比革命還要緊』……屠格涅夫曾寄書於一熱烈的革命家說,『你想革命的要素存在於人民中,其實恰恰相反,我可以斷定革命這樣事體,從他的真意思、最大的意思解釋起來,只存在於知識階級的少數人』……當時俄國人民總有一億農民,極其守舊,故革命運動的事也不能不單在少數知識階級的肩上……大俄羅斯自成一部或存或亡都為一體,在其六千萬人口中約有百分之十是構成俄羅斯革命的要素的,其餘都與革命沒有關係……俄羅斯中心只在大俄羅斯一部分,而在大俄羅斯中革命的中心勢力又只在大俄羅斯全人口中少數的知識階級」,俄羅斯革命1917年後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派已經不成為重要元素,「自由主義派、社會主義派是近年來促進俄國革命的兩大勢力」,在介紹勞農政府組織及其中心人物方面主要是列寧,此外還涉及了盧那察爾斯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八人(沒有論及斯大林)13。而且,在《社會主義下之實業》(1921)中李大釗還深刻指出,「俄羅斯既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何還能振興實業?單就鐵路一端二論,蘇維埃政府於過去三年間,添造鐵路五千七百俄裏。現在還派員四處測繪,預備再築新路兩千俄裏,今年年內即可通車……中國共和現在已竟十年,添造的鐵路在哪里?且俄國於改良農業,開墾荒地,都有切實之計劃。中國以農立國,然而農業腐敗得不堪過問」,進而強調中國「用資本主義發展實業,還不如用社會主義為宜」14,此後在《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北大經濟學半月刊》1922年1月16日)中,李大釗贊同性地介紹了社會主義經濟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等各環節上的計劃經濟特點。
李大釗如此巧妙地把俄國革命與中國實踐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問題聯繫在一起,大大提升了正面塑造的蘇俄形象,也激發了國民關注蘇俄革命理論和歷史之熱誠,新青年很快把反對西方、否定資本主義、對抗私有制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現象當作馬克思主義來推崇,並且運用於中國實踐。由此,克魯泡特金的學說在中國風行一時:《俄國文學的理想與現實》在文學界流行,一系列無政府主義著作尤其是《互助論》則在理論界盛行。《互助論》最早由周佛海作為社會主義經典文獻引進(1921年商務印書館初版):該書用無政府主義思想敘述社會發展歷程,主張人類以互相幫助的本能就能建立和諧的社會,勿需建立權威和制度。這原本是俄國民粹主義者借用鄉土觀念,抵抗外源性現代化運動中政府推行西化、建立國家權威的烏托邦,可是此說在中國卻極有影響力:1923年10月出第三版、1926年6月出第四版、1930年《萬有文庫》第一輯收入該作(重譯)、1933年1月出第五版。這廣為流傳的思想和俄國民粹主義一道召喚著進步青年,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李維漢等人讀了這類書刊,覺得共產主義美妙遠景非常好,應該作為奮鬥目標,並紛紛實踐那些烏托邦幻想;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介紹日本「新村」試驗、毛澤東讚賞岳麓山建設新村、惲代英準備組織這種新村等。特別是,李大釗1919年2月在《晨報》上發文《青年與農村》稱,「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俄國今日的情形,縱然紛亂到甚麼地步,他們這回革命,總算是一個徹底的改革,總算為新世紀開一新紀元……他們有許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拋棄了,不憚跋涉艱難辛苦,都跑到鄉下的農村裏去,宣傳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道理……在那陰霾障天的俄羅斯,居然有他們青年志士活動的新天地,那是甚麼?就是俄羅斯的農村。我們今日中國的情況,雖然與當年的俄羅斯大不相同,可是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裏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做開發農村的事情,是萬不容緩的」,中國是農業國、勞工階級主題是農民,農村黑暗、愚昧、民主政治精神無法深入,現代青年去農村裏可以大有作為、在都市里呆下去反而會平庸,故熱切呼喚「在都市里飄泊的青年朋友們!你們要曉得,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裏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清潔。你們為何不趕緊收拾行裝,清結旅債,還歸你們的鄉土?……只要知識階級加入了勞工團體,那勞工團體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還了農村,那農村的生活就有了改進的希望;只要農村生活有了改進的效果,那社會組織就有了進步了」15;1919年7月他又在《每周評論》上著文《階級競爭與互助》,用「互助論」來補充階級鬥爭學說,說「這最後的階級競爭是改造社會組織的手段,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類精神的信條」;《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也隱含著類似思想。很顯然,這些既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強調社會建設的列寧主義,而是主張革命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和來自日本的馬克思主義之混合,由此在意識上逐漸遠離了科學與民主的啟蒙精神,瞿秋白稱新文化運動「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而不能成就」(《新青年‧新宣言》)、鄧中夏斷言新文學是「驚醒人們有革命自覺的最有效用之工具」(《貢獻於新詩人之前》)等逐漸成為流行觀念,由此無暇分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潮之差別16。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過後,這種情形幾乎改變了中國知識界共同熱情變革中國的結構,1931年楊東蕙在《本國文化史大綱》如實描述了這樣的分化:「不到幾時,《新青年》受了蘇俄革命的影響,便斷片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學說;而李大釗竟在北大講授唯物史觀。後來思想分野,李大釗和陳獨秀便信奉馬克思主義,而成為中國某某黨的指導人物;胡適之一派邊信奉杜威的實用主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17,即中國進步知識界發生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分裂。
十月革命、蘇俄新文學和俄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贏得了極大的聲望,也促使人們熱情想像蘇俄政權領導人列寧。1918年創刊的《每周評論》在其發刊詞中鄭重聲明,三年前中國認為美國總統威爾遜是「世界第一好人」,現在北大進行「世界第一偉人」民意測驗,497張票中列寧獨得227票居第一,第二位的威爾遜僅得51票;列寧去世(1924年1月24日)引發中國人關注列寧又一輪熱潮,一周後惲代英便在《中國青年》第十六期上發文《列寧與中國的革命》,塑造了一個有知識、有能力、有品格的革命家和學者列寧形象,認為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很有指導意義的列寧;3月15日出版的上海大學學生主辦的《孤星》旬報第四期發表《追悼列寧專號》(陳獨秀之文《列寧之死》便刊於其中);3月16日一批知識份子在北京集會追悼列寧,李大釗發表演講《列寧不死》,為列寧之言「苟能成就世界革命,即使俄羅斯民族蒙莫大的犧牲,所不敢辭」激動不已18。在列寧逝世周年紀念日,陳獨秀在《嚮導》周報第九十九期發文《列寧與中國》,塑造了一個同情中國、支援中國革命的國際無產階級領袖形象。與此同時,胡愈之在《東方雜誌》連續發文:在《列寧與威爾遜》中,一方面介紹代表西方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及其著名的巴黎和會十四條如何成為謊言、自由主義如何破產,另一方面介紹列寧如何從「過激派亂黨」頭領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領袖,在對比中強有力地張揚列寧的偉大;在《諸名家的列寧觀》中,彙集了高爾基、英國社會主義作家和《先驅日報》主筆蘭斯伯雷(G. Lansbury)、法國工團主義者沙列爾(G. Sorel)、英國學人羅素、俄僑拉巴爾德(C. Rappaport)等人的列寧觀,或者他們與列寧交往所得的直觀印象,如在高爾基看來,「列寧一生的大志,是在把全世界的勞動者,從奴隸制和資本主義拯救出來,以建立大同社會,『世界是我的祖國,全人類是我的兄弟,行善是我的宗教』,這幾句著名格言就是列寧的座右銘……列寧乃世界上最受人恨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受人愛的人……我這樣描寫列寧,可不是因為我同意於他的一切主張──有許多基本事情,我卻不能同意──不過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好人,是一個言行相符的好人」;羅素莫斯科之行和列寧有直接交往,發現他英文很好(不需要翻譯),「他好像一個大學教授,一方面希望人家對於他的學說能夠了解,另一方面因為人家誤解他的學說或反對他的學說,又非常氣憤;大學教授極喜歡向別人講道理,列寧也是這樣。我覺得他對大多數人都看不上眼,他簡直是一個文化貴族……據我猜想,他具有這般能力,是從誠實、勇敢、堅定的信仰──就是對馬克思福音的信仰,這種福音很可以替代基督教殉道者對極樂園的希望,不過利己觀念比較少一點罷了──這幾種好處得來的」;拉巴爾德說,「和列寧相識遇巴黎會議上,當時我對於這位勞農政府領袖所得的最深印象是他的思想的清楚與堅定」。在《列寧及其後》中,胡愈之認為列寧無論功過如何,對於當代和未來世界的影響可能沒有人能與之相比,「列寧的革命事業可以說已做到六七分,還剩著三四分,後人只需要遵著列寧的遺規幹去就是了」19。1926年1月21日北京各屆六百餘人雲集北大紀念列寧去世兩周年,事後《政治生活》雜誌第六十六期推出《列寧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紀實》,李大釗發表演說,「因列寧先生想到中山先生」並對他們的革命精神、毅力和影響力等進行了比較,稱「列寧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精神!我們應該服膺這種精神!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策略。中山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革命的理論與策略。在理論上,中山主義與列寧主義是可以聯合成一貫,策略上是能連貫一致的。所以列寧主義者可以說就是中山主義者,中山主義者就是列寧主義者!他們的主義同是革命的主義。假如中山生在俄國,他一定是列寧;假使列寧生在中國,他也一定是中山!他們主義表面看起來不同,實在是環境的不同。中山與列寧的目的相同,可惜乎環境不讓他實現得如列寧那樣成功!他最初想聯合菲律賓,先幫助他們革命成功,再來實現中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最初有日本的革命黨人。這都是他聯合世界革命的表現,與列寧的主張相同……現在無論列寧主義者或中山主義者讀不應該兩下分離!在座的同志們,你們不管是列寧主義信徒,中山主義信徒,應該緊緊的聯合起來!」20。李大釗的這種類比,1925年4月6日張聞天發表的《追悼孫中山先生》(重慶《南鴻》周刊第2期)已嘗試了,並在比較兩人留下的不同遺產(統一的蘇維埃和分裂的中國)中呼喚俄式革命。很有親和力的列寧形象就這樣生成了!以後把列寧主義─斯大林學說作為馬克思主義一個部分的做法那也就不令人意外了:陳獨秀稱,「列寧主義自然就是馬克思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到了列寧,則更明瞭確定了,周密了,也擴大了……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殖民地即被壓迫的國家,他們的民族運動,只有依照列寧這樣偉大的周到的意見而行,才能夠徹底的解決,才能夠得著真正的自由,這是一件最明白無疑的事」,孫中山在臨終致蘇聯遺書中也有同感,認為蘇俄「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於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並希望國民黨能按這個規則進行民族革命運動21。進而,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共產國際、倡言「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的列寧之作《國家與革命》(1930年上海中外研究學會翻譯出版)、重新設計「馬列主義體系」《辯證法唯物論教程》(1931年在米丁領導下共產主義科學院列寧格勒分部為蘇聯黨校及高校編撰的教材,1936年延安翻譯出版該作)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39年中國出版社初版、1948年時代書報出版社再版、1949年上海中國出版社和北京解放社出版幹部讀本)、把計劃經濟等於社會主義的斯大林之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年人民出版社)等,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也就自然而然了。
更為重要的是,對列寧的認同,延伸出把蘇俄首先是維護自己利益的國際共運原則當作經典馬克思主義而加以確認,並相信勞農新政府是按這種國際共產主義原則無私處理中國問題的。1919年7月25日的《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和第二年9月27日的《蘇俄政府第二次對華宣言》引起中國社會激動,特別是蘇俄利用共產國際原則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後,中國不少人更相信蘇俄對華的誠意,如孫中山稱蘇俄「不但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幼,主持公道」22。周作人在那篇著名的《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中稱,「俄國從前以侵略著名,但是非戰的文學之多,還要推他為第一。所謂獸性的愛國主義,在俄國是極少數;那斯拉夫派的主張復古,雖然太過,所說俄國文化不以征服為基礎,卻是很真實的」23。1923年1月16日孫中山與蘇俄政府在華代表越飛簽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宣稱,「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並同意中東鐵路共管,特別是「越飛君正式向孫博士宣稱,俄國現政府絕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24。瞿秋白的《赤都心史》(1923)熱誠記錄了盧那察爾斯基的東方觀:「因為俄國跨歐亞,和東方古文化素有接觸;革命前俄國境內各民族也是被壓迫的,對於『東方』極有同情。況且蘇維埃俄國不像其他歐美各國妄自尊大,蔑視東方,我們是對於東方各民族極端平等看待,對於他的文化尤其有興趣。現在極注意於促進兩民族的互相了解,採用他的文化,已經設一東方學院。東方文化之『古』、『美』、『偉大』、『崇高』,詩文哲學,興味濃郁」25。這年底,陳獨秀發文《蘇俄六周(年)》全面反駁國內非俄之言,斷稱新俄不會侵略中國和世界、蘇俄社會各方面都在趨向完美,而且「我們革命十二年如今越鬧越遭,俄羅斯革命才六年,為甚麼能有這樣的建設?主要的原因是有一個幾十萬人的過激黨,負了為國家由破壞而建設的大責任同心戮力的幹。所以疑謗蘇俄的人,每每只是疑謗蘇俄的過激黨;可是感佩蘇俄的人,也應該首先感佩蘇俄的過激黨」26。第二年底,李大釗在蘇俄感受到新俄和紅色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從而更堅相蘇俄奉行的是淡化民族國家觀念的國際共運原則27。更為重要的是,1928年8月底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六大」第四十三次會議上宣讀的一項關於東方各國共產黨關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聲明,是瞿秋白起草的:「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祖國的蘇聯的發展問題,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是國際共運極為重要的問題……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是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反帝起義和反帝戰爭的中心。」28理論上是如此憧憬蘇俄,在中俄關係所遭遇的實際問題上,中國進步知識界也是這樣樂觀。針對《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簽訂未果事件,1924年3月陳獨秀在《中俄會議之成敗》(《嚮導》周報第五十八期)評述會談破裂,「好的方面是:蒙古人民免得馬上要受中國軍閥的統治及中國兵的姦淫焚掠;在中國兵未去之前,他們可以多得時間充分準備抗鬥自衛的武力」,在《評中俄協定》(《嚮導》周報第五十九期)中繼續稱,「對於這次中俄協定,也有一點不滿意,就是蘇俄承認中國在外蒙之主權,輕輕將外蒙獨立的國民政府否認了。或者蘇俄也有一種苦心,以為蒙古獨立的力量還不充分,與其放任了為帝國主義的列強所取,不如歸之中國,中國的侵略力量究竟不及列強」,在《嚮導》周報第六十八期發文《中俄協定簽字後之蒙古問題》(1924)更強烈反對這種把外蒙歸還中國的協定。以至於1925年發生蘇俄是友是敵的大爭論時,張溪若指出「在近日人人對這個重要問題不敢有所表示的時代」,《晨報》敢站起來發表反對意見,「令人非常欽佩」(1925年10月8日《晨報副刊》)。
事實上,蘇俄對華政策首先是要解決新生蘇維埃共和國安全和生存、民族利益問題,其次才是國際共運,列寧的共產主義思想和國際共運原則在勞農新政權中落實的程度並不高,俄羅斯帝國中心論不僅主導著蘇俄建構過程,而且推延及世界,尤其是成為處理與中國關係問題的原則:1919和1920年蘇俄政府兩次對華宣言發布之間,蘇俄獨自派紅軍進入屬於中國版圖的蒙古並在中東鐵路問題上繼續帝俄政府政策;1923年蘇俄政府任命越飛為駐華特命全權大使與孫中山和吳佩孚談判,很大程度上是看重他們乃中國實力派人物;1924年蘇聯政府名義上廢除帝俄政府外交政策,但與國民政府繼續簽訂共管中東鐵路協約,引起中國民眾的憤怒,1929年國民政府迫於民眾壓力而解除這一不平等協約,差一點引發戰爭並使得國民群情激奮29;至於蘇聯利用共產國際的話語霸權對中國革命進程進行干預,使中國形勢變化服從於蘇俄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那已經是人所皆知的事實。後來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中推行蘇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擴張蘇俄國家利益那就更如此了,如斯大林曾聲言,「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因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國家。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不捍衛蘇聯,就不能捍衛並推進世界革命運動」30,他還譏諷恩格斯批評帝俄之作《沙皇俄國的對外政策》(1889)「寫得有點興奮,所以一時忘記了一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反對把他譯成俄文發表。至於在維護國際共運的名義下,1938年強行解散波蘭共產黨、1943年為了和西方國家合作解散了共產國際、戰後為了同西方陣營對抗又在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名義下恢復共產國際(實際上成為蘇聯指揮和控制各國共產黨的中心)、東歐大批知識份子和黨的中高級幹部被清洗或監控等,勿需贅言1924年蘇聯政府名義上廢除帝俄政府外交政策,但與國民政府繼續簽訂共管中東鐵路協約,引起中國民眾的憤怒,1929年國民政府迫於民眾壓力而解除這一不平等協約,差一點引發戰爭並使得國民群情激奮31;至於蘇聯利用共產國際的話語霸權對中國革命進程進行干預,使中國形勢變化服從於蘇俄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那已經是人所皆知的事實。後來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中推行蘇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擴張蘇俄國家利益那就更如此了,如斯大林曾聲言,「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因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國家。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實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不捍衛蘇聯,就不能捍衛並推進世界革命運動」32,他還譏諷恩格斯批評帝俄之作《沙皇俄國的對外政策》(1889)「寫得有點興奮,所以一時忘記了一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反對把他譯成俄文發表。至於在維護國際共運的名義下,1938年強行解散波蘭共產黨、1943年為了和西方國家合作解散了共產國際、戰後為了同西方陣營對抗又在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名義下恢復共產國際(實際上成為蘇聯指揮和控制各國共產黨的中心)、東歐大批知識份子和黨的中高級幹部被清洗或監控等,勿需贅言33。
二
瞿秋白在給《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北京新中國雜誌社1920年7月出版)所寫的《序》中就如是說道:「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在中國卻已似極一時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思想都受它的影響。大家要追溯其遠因,考察其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於俄國,都集於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裏,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裏開闢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潰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於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這種情形與社會塑造「革命」、「進步」和「正義」的蘇俄或列寧形象氛圍相交融,進而導致蘇俄社會主義實踐和列寧思想幾乎全部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並以此作為接受和理解俄國文學的指導思想。
在這種局勢下,列寧關於文化和文學的論著,尤其是列夫·托爾斯泰之論和《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在中國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疆域。托爾斯泰作為俄國偉大作家之一,從1870年代以來就成為社會關注人物,尤其是在他八十壽辰和1910年去世之際更是出現了解讀這位作家的熱潮,包括普列漢諾夫之《托爾斯泰與自然》、勃洛克之《俄羅斯的太陽》(1908)、梅列日科夫斯基之《列夫‧托爾斯泰與教會》(1908)和《列夫‧托爾斯泰與革命》(1908)(特別是他1909年推出的力作《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羅贊諾夫之《托爾斯泰》和《兩個偉大世界之間的托爾斯泰》(1908)、維·伊凡諾夫之《托爾斯泰與文化》(1911)等,這些都是極其深刻解讀托爾斯泰的力作。其中,伊凡諾夫稱「列夫‧托爾斯泰離家出走了,很快的也就離開了人世,──這是整個人的兩次最終解脫,也是一個人的雙重解放──引起千百萬人心靈的最虔誠的震撼」34。尤其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托爾斯泰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公共事業》1921年1月總第189期)中更深刻地指出,托爾斯泰與布爾什維克革命之間存有複雜的關係,「在倫理學上,托爾斯泰並不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因為他是『勿以暴力抗惡的』,絕對否定暴力的,而布爾什維克是絕對的暴力分子。但是,否定暴力把托爾斯泰與布爾什維克區別開來了,在同等程度上與我們區分開來了:要知道,我們並不否定強力,我們是用暴力抗惡的。所有問題在於程度上:布爾什維克的暴力是無限的,而我們的暴力是有限的」,「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上,托爾斯泰是『資本家』和『地主』,他的所有欲望就是舊俄羅斯的欲望。但是他破壞了這個欲望,就像布爾什維克一樣如此毅然決然地粉碎、滅絕了這個欲望」,「在美學和形而上學上托爾斯泰是最切近布爾什維克的……否定任何文化,力求簡易、平凡,最終是野蠻意志」,「興奮的破壞即興奮的建設:這就是巴枯寧、列寧、托爾斯泰、普加喬夫、拉辛等人不朽的俄羅斯(вечнорусское)」,「俄羅斯的『野蠻意志』是否能創建全世界意志呢?可能的。在俄國是托爾斯泰,在歐洲是盧梭。盧梭和托爾斯泰是兩次革命的起因」,「托爾斯泰和誰同在──這個問題只有在宗教中才能解決。因為我們只要遠離了宗教,他也就離我們而去;當我們不回歸宗教的時候,他也就不會回到我們身邊」,「『勿以暴力抗惡』在倫理學上是令人疑惑的真理,而在宗教上則是毫無疑義的。從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到孟什維克的暴力走的都是這條道,而宗教目的則絕對否定暴力的」35。由此可見,在這眾多有價值的聲音中,列寧的五篇托爾斯泰論是其中重要論述之一。可是,現代中國從1920年代開始就只是注意到了列寧的文章並多次翻譯之,如鄭超齡1925年就譯出《托爾斯泰與當代工人運動》刊於《民國日報·覺悟》(是年2月12日)、《文學周報》第333-334期合刊(1928年9月9日)作為「托爾斯泰百年紀念特別號」收錄有胡劍譯的《托爾斯泰論》、是年嘉生(彭康)譯出《托爾斯泰──俄羅斯革命的明鏡》(《創造月刊》第2卷第3期)、兩年後何畏又重譯該作(《動員》第二期,1930年9月),1933年1月胡秋原又再譯《俄國革命之鏡的托爾斯泰》(《意識形態季刊》1933年第一期),是年5月北平《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二期刊發了陳淑君譯的《托爾斯泰論》(包括《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托爾斯泰》、《托爾斯泰與勞動運動》和《托爾斯泰與時代》等),12月何思敬翻譯了《L.N.托爾斯泰與他的時代》(《文藝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瞿秋白翻譯了《列甫‧托爾斯泰像一面俄國革命的鏡子》(《文學新地》創刊號),1937年初上海亞東圖書館所出版的《恩格斯等論文學》(趙繼芳譯)中收錄有列寧論托爾斯泰三篇文章,1943年戈寶權系統翻譯了《列寧論托爾斯泰》(連載於重慶《群眾》周刊第八卷第六、七期合刊至第十期),1947年北泉翻譯了列寧的《論托爾斯泰》(《蘇聯文藝》月刊第二十六期)等等。而上述其他很有價值的托爾斯泰之論基本上無人關心,對托爾斯泰作品在十月革命後曾被查禁之事也沒特別在意,儘管周作人在《托爾斯泰的事情》(1924)中已提及此事:「托爾斯泰著作被俄國社會主義政府禁止,並且毀書造紙,改印列寧著書」,當時中國知識界還不相信,「有些人出力辯護,我也以為又是歐美帝國主義的造謠,但是近來據俄國官場消息,禁止乃是確實的」36。對列寧的托爾斯泰之論這類成規模甚至是系統化的翻譯,與對其他篇章的翻譯相配套,如《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的漢譯先後為《中國青年》(1926年底)、《拓荒者》(1930年初)、《解放日報》(1942年5月14日)、《群眾》周刊(1944年7月)等刊出,1933年神州國光社出版了王集叢翻譯的《列寧與藝術》就「全部搜集了列寧對於藝術的一切意見,而且把這些意見組成了一個系統的體系」。其實,托爾斯泰超過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其文學文本、文藝理論、政論、散文、書信和日記等,連同他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聲望,共同顯示出:他遠不只是反映了宗法制農民對傳統莊園制度和西式改革的憤怒而又無可奈何的情緒,而且還顯示出俄國傳統知識份子面對現代化進程的責任感和複雜思考,特別體現出俄國斯拉夫民族認同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之間的融合和衝突並存、現代性在俄國受到地方性的抵抗或傳統俄國向現代俄國轉化的困難程度等。列寧作為革命家對托爾斯泰的認識,多著眼於作家的現實性意義和社會學價值,而且這方面的深刻性無出其右者,但沒來得及顧上作家的知識份子身份、創作中的民族性訴求、超越階級的現代性和傳統性等重大問題,即使是「托爾斯泰主義」也不等同於用宗教理解世界和處理現實問題的落後思想,而是包含有考慮宗教和東方文化應付現代性問題的價值。中國把列寧的托爾斯泰之論作為認識全部托爾斯泰的指導思想,並不斷提升這種認識的普遍性價值和根本性意義,又拒絕觸及其他人論托爾斯泰的資源和完整的托爾斯泰(紀念托爾斯泰百年而編輯的全集是九十卷),這不僅在事實上縮小了托爾斯泰的多方面意義,而且把列寧批評托爾斯泰的創造性方法論價值也簡化甚至僵化了。
也正因為如此,促成了中國引進外國文論的格局不再是世界性的、多元化的,而改為以俄國文論為主體,並且進一步縮小為蘇俄文論為正宗,甚至以為蘇俄文學批評和理論一定就是馬列主義的。普羅文學時期,從蘇俄回國不久的蔣光慈之作《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1924)和《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1927)等著名論著,連同茅盾的《論無產階級藝術》(1925)這類重要篇章,就已經顯露出進步知識界對蘇俄文論的強烈興趣,細讀這些篇章還可以發現,中國這類宣導普羅文學的著述,基本上是深受蘇俄無產階級文化派之說影響的結果;郭沫若、成仿吾、蔣光慈、李初梨、馮乃超等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借助波格丹諾夫的「組織生活」理論、無產階級文化派尤其是拉普庸俗社會學思想,名義上熱情宣導無產階級文學,實質在中國文壇和理論界推行極左思想,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學及其作者等遭不切實際的批評、否定,挑起革命文學論爭,魯迅等人逼迫關注蘇俄新文學和理論,由此啟動了他和馮雪峰合作編輯《科學的藝術論叢書》(最初計劃出版十四種),實際出版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魯迅譯)、《藝術與社會生活》和《藝術與文學》(馮雪峰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之社會的基礎》(魯迅)和《文學與批評》(魯迅)、波格丹諾夫的《新藝術論》(蘇汶譯)、弗里契的《藝術與革命》(馮乃超譯)等七種,以此提供論爭的水準;1930年初左聯成立,隨之成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開始有計劃翻譯地從俄文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論,於是便有了上文系統引進列寧的托爾斯泰論,尤其是更積極引進左傾理論,如馮雪峰譯了法捷耶夫那宣導無產階級文學應該為辯證唯物論而鬥爭的《創作方法論》(1931)、周揚等人及時引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些過程,製造了中國式的「馬列文論」,誠如向培良的《盧那卡爾斯基論》(1933)所稱,「馬克思派的藝術論,即以藝術與其他文化政治等同為上層建築,以經濟的生產力為其基礎而相應地變化的理論,以馬克思主義及波爾雪位克(布爾什維克)的政策為骨幹來處理藝術及藝術論,在國內曾一時變得非常流行。以魯迅等人之努力,此派藝術理論譯過來的非常之多,成為藝術底流行物了」37。有意味的是,普列漢諾夫得到了特別重視,不僅他的很多文獻被譯過來了,而且他的思想也得到運用:瞿秋白在翻譯普列漢諾夫論易蔔生、別林斯基和法國文藝等名作基礎上寫就了《文藝理論家普列漢諾夫》(1932年,後收於《海上述林》上編),馮憲章、黃芝威、韓起等人譯介了蘇聯對普列漢諾夫研究之論,魯迅從日文轉譯的普列漢諾夫《藝術論》包括《論藝術》、《原始民族的藝術》和《再論原始民族的藝術》(上海光華書局1930年7月版),並在此基礎上寫成《〈藝術論〉譯本序》,稱作者乃俄國馬克思主義先驅,其藝術論為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和社會學美學的古典文獻,並肯定文藝作為社會現象而有階級性之論,還把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美學思想「並非人為美而存在,乃是美為人而存在」延伸為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美學綱領38。不過,沒人認真分析普列漢諾夫何以從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轉變為孟什維克的複雜原因,胡秋原1929-1930年編著於日本的《唯物史觀藝術論──樸列汗諾夫及其藝術理論之研究》(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年12月)這部專論普列漢諾夫藝術理論極有成就之作,在《編後記》中甚至把弗里契這位左傾理論家視為普列漢諾夫真正繼承者。這些與早年李大釗主持的《晨報》副刊「馬克思主義研究」專欄少有馬克思本人的經典著作一樣(刊載的是日本左翼學者河上肇著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甚至在理論水準上並不比1903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福井准造的《近代社會主義》漢譯本更高(當時譯者趙必振視之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只不過當時缺乏十月革命契機,這些譯介沒有產生實際的影響。今天回過頭閱讀當時頗有影響的「馬列文論」譯作,包括上文未提及的《伊里幾的藝術觀》(裘耐夫作、沈端先譯,1930)、《文學的黨派性》(川口浩作、張英白譯,1933)、《伊利奇的高爾基評》(特裏方諾夫作、孟式鈞譯,1936)等篇章,我們可以發現:不少俄文原作早已成為歷史陳跡,譯作同樣問題多多。但這些翻譯顯示了中國引進「馬列文論」的基本格局:不少是經由日文左翼理論家的仲介而來的(而日本譯者大多是激進的理論家,這點連同日文自身的局限性,給中國再度轉譯帶來了更多的誤讀),即使是直接來自俄文的,也少有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經典作品,基本上是譯介和更激進的詮釋蘇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
也正是在這種引進「革命文論」潮流中,蘇俄不少人物在中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著名理論家,如波格丹諾夫(A. Богданов,1873-1928)這位革命活動家和經濟學家之作《新藝術論》由蘇汶譯出、上海水沫書店作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三出版(1929年5月初版、第二年再版),譯序稱作者乃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藝術的人;盧那察爾斯基更是如此,魯迅翻譯了他的《托爾斯泰與馬克思主義》(《奔流》雜誌第1卷第7-8期,1928年底1929年初)、《藝術之社會的基礎》和《文學與批評》(上海水沫書店,1929),朱鏡我譯了《關於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底任務之大綱》(《創造月刊》第2卷第6期,1929年1月10日)等,黎君亮的《盧那卡爾斯基的蓋棺試論》(1932)稱「他的理論的『深』與『博』以及普遍都做到了,但是還不曾完成;這原因,恐怕是社會主義本身沒有得到完成的緣故」,「他只是一個發言者、論文家,他闡明了許多片斷的真理。但是他沒做到的功夫,就是他美學上的理論還付闕如」39,一時興起了盧那察爾斯基熱。尤其是弗里契(Вл.М.Фриче,1870-1929)這位試圖用階級論研究西歐文藝和藝術社會學問題的蘇俄早期文藝理論家,「在論述美學和現代文學等論述中,採用的是庸俗社會學的方法論」(《蘇聯百科辭典》及再版本),在現代中國極有影響:1921年8月胡愈之在《鮑爾希維克(布爾什維克)下的俄羅斯文學》(《東方雜誌》第十八卷第十號)中介紹了弗里契文藝學和文學批評貢獻;其力作《藝術社會學》作為庸俗社會學的代表作,在中國廣為傳播,如上海水沫書店1930年出版了劉吶歐譯本(作家書屋1947年8月再版了譯作,譯者改署天行)、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年5月推出了胡秋原譯本,兩譯者在譯本的前言或後記中分別提及弗里契作為學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偉大性,高度讚賞該作乃與普列漢諾夫研究同等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科學論著,劉氏在《後記》中稱該書在學術價值上是「紀念碑性的」,白葦在胡秋原譯本序中稱該作乃解決藝術發展這一最難問題的「基礎著作」,「研究之細密、資料之豐富,實藝術理論上從未有之大觀,而亦本書價值之不可限量的」,胡秋原更是聲稱該書乃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上劃時代著作。這樣評價是很普遍的,諸如(馮)雪峰翻譯了他的《藝術社會學之任務及諸問題》(《萌芽月刊》創刊號,1930年元旦)並正面肯定從中可見出《藝術社會學》之概要,儘管作者在此是用階級論分析藝術發展史,主張「藝術是組織社會生活的特別手段」、社會階級鬥爭會「由種種形式反映到藝術上來」等,而且這期創刊號上還刊載了他所翻譯的藏原惟人更為左傾之作《藝術學者弗里契之死》;馮乃超、蔣光慈、許幸之分別翻譯了其《藝術家托爾斯泰》、《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現代俄國文學》、《藝術上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同化》(載於《文藝講座》第一冊,1930年4月),這些無一不是立足於庸俗社會學的。宋陽(瞿秋白)在《論弗里契》(《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1932年12月15日)中盛讚作者乃用唯物辯證法研究文藝科學的第一人,比普列漢諾夫進步之處在於「更徹底地了解文藝和階級關係」,能在階級鬥爭學說中研究藝術,承認階級鬥爭學說乃「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之基礎」,批評作者還保留有普列漢諾夫的「科學文藝批評」這種客觀主義之不足、追求普遍真理的「邏輯主義」之不足,認為只有黨派的文藝批評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資產階級立場不許批評家接近事實、無產階級黨派立場是最覺悟了解到無產階級利益的立場(斷言「這是合於客觀事實的立場」)。1940年代這種情形更為普遍勒,如蔡儀在《弗里契的〈藝術社會學〉方法略論》(上海《文訊》月刊第九卷第二期,1948年8月)雖批評弗里契有機械論之不足,但他批評的正是這位理論家最有見地之處,即歷史發展會出現社會結構迴圈或類似現象,進而導致藝術類型有重現或對應的可能,褒揚弗里契的卻是「就藝術社會學的發展而言,他的著作可以算作是一座里程碑」,並不在意他在文藝社會學上的不足。
與之相伴隨的是,192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文藝論爭和政策在中國幾乎得到了與蘇俄同等的認同,並且也以為這就是無產階級文藝的進展:編譯數量之大、速度之快、呼應之熱烈難以言說。任國楨編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北新書局1925年8月版)包括櫧沙克的《文學與藝術》、阿威爾巴赫等人的《文學與藝術》、瓦隆斯基的《認識生活的藝術與今代》等,而這些在蘇俄也是剛問世不久。編譯者在書前《小引》中云,編譯本集意在介紹新近蘇俄出現的「列夫派」(左翼藝術陣線)、「納巴斯徒派」(на посту,今譯成崗位派)、「真理報」派(蘇聯官方派)等三派文藝之爭基本情形;魯迅在《前記》中補充道,即十月革命後印象派(說成是「想像派」)和未來派執文壇牛耳、1921年後左翼文學興盛,認為「列夫」對無產階級革命藝術的追求很真,對這派信奉理性主義、反對文學的想像性、主張「事實文學」、鼓吹藝術與生產相結合的「社會訂貨」等,在具體藝術實踐上追求先鋒主義這類重要內容,魯迅沒有明確表達見解。據日本馬克思主義者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的日文本,魯迅輯譯了《文藝政策》(上海水沫書店1930年6月版),它包括《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1924年5月聯共中央關於文藝政策評議會的速記稿)、《觀念形態戰線和文藝》(1925年1月無產階級全俄大會決議)、《關於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政策》(1925年7月1日《真理報》)等,還有充滿庸俗社會學之嫌的藏原惟人之譯序和日本岡澤秀虎之作《以理論為中心的俄國無產階級文學發達史》(該文基本上是對蘇聯主流文藝史觀的編譯,即反對流亡國外的白俄作家和國內同路人作家、肯定「列夫」和「拉普」),對文集中「文學是階級鬥爭的強有力武器」、主張唯有蘇維埃文學才是最有生命力等極端觀念,魯迅在後記中沒有明確批評。此前畫室(馮雪峰)曾抽譯《新俄文藝政策》(上海光華書局1928年9月版),魯迅譯文曾在《奔流》上連載,岡澤秀虎之文也由陳雪帆(陳望道)譯出連載於《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三至九號(1929年3-9月),洛文翻譯了日本上田進之作《蘇聯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的現狀》(《文化月報》第一卷第一期,1932年11月),首次把斯大林的「文藝學科的列寧主義階段」引進了中國。1932年4月23日聯共中央發布《關於改組文藝團體的決議》,決定取消阻礙藝術發展的思想狹隘的無產階級作家團體(「拉普」)、成立統一的蘇聯作協,是年10月底11月初全蘇作家同盟組委會召開第一次大會,秘書長弗‧吉爾波丁發表報告《十五年來的蘇聯文學》。很快的,華蒂(葉以群)編譯了《全俄作家同盟組織委員會》(《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至六期合刊,1932年12月)、起應(周揚)編譯了《十五年來的蘇聯文學》(《文學》第一卷第三號,1933年9月),予以積極回應。而且,還直接與蘇聯作家發生組織上的聯繫:1927年莫斯科建立「國際革命文學事務局」,把國際普羅文藝統一在共產國際之下(「就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共產國際一樣,文學上也要建立文學國際」)、解決國際普羅革命文學的發展和組織問題,打算在世界各國建立支部,中國左聯被認定為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一個支部──中國支部;1930年在哈爾科夫舉行第二次國際革命作家代表大會,大會向世界各國支部提出「『假如帝國主義向蘇聯作戰時,你們怎麼辦呢?』正確回答是『保護十月革命,保護蘇聯」,儘管中國處境遠比蘇聯要困難得多,蕭三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並在給左聯的《出席哈爾科夫世界革命文學大會中國代表的報告》中卻對此做了積極的反應(《文學導報》第一卷第三期,1931年1月9日)。由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此後能在中國被演繹一番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1933年茅盾在《讀了田漢的戲曲》中提及田漢《梅雨》除了「『革命的浪漫主義』之外,還配合這『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40;上海《現代》雜誌第三卷第六號(1933年10月)刊發了華西裏可夫斯基之作《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論》(森堡譯),不久北平《京報‧沙泉》刊出式鈞之作《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地特質》,此乃盧那察爾斯基在蘇聯作協籌委會上的報告記錄(原文《蘇聯戲劇創作的道路和任務》,後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題發表)之摘譯,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解為是對拉普「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替代,是馬恩所理解的現實主義。期間,唯有周起應(周揚)的《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現代》雜誌第四卷第一號,1933年11月1日),認真闡釋了盧那察爾斯基和吉爾波丁等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論,其他的,如吳春遲之譯文《社會主義的藝術底風格問題》(《文學》第一卷第六號,1933年12月)、余文生之譯文《蘇聯的演劇問題──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文學和戲劇》(《文學新地》創刊號,1934年9月)等大部分譯文或論文對這個問題普遍語焉不詳。此後,同步性譯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討論、斯大林獎這一蘇聯國家獎而非世界性獎把丁玲和周立波延攬其中等,這在客觀上使中國文學成為蘇俄文學的一種外延擴展或成為蘇聯文學的一個部分,也就勢不可擋了。
事實上,列寧試圖終止一些激進的左翼文學青年要培育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之願望,托洛茨基和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沃隆斯基等人批評不可能產生無產階級文化的主張,自1925年6月公布的《關於黨在文學方面的政策》(布哈林執筆)之後,反而變成了烏托邦:承認創造無產階級文學的可能性,並首先支持持這種創作傾向的理論、流派和團體,而且即使1932年解散了宣導辯證唯物主義的拉普,但也沒有扭轉這種趨勢。
也正因為對蘇聯主流文學和理論的強烈認同,導致1920年代後期以後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文學的選擇中左翼文藝佔了相當的比重,諸如思明的《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概況》(《文學導報》第一卷第四期,1931年9月)、毛秋白的《現代德國的勞動文學與普羅文學》(上海《新中華》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93年3月)在很長一段時間影響了人們對德國文學的判斷,幾乎改變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對德國文學接受的方向。更突出的是對日本普羅文藝鋪天蓋地質譯介,諸如魯迅翻譯了片上伸之作《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1929年2月14日譯訖)、陳勺水先後在《樂群月刊》上刊發了天青三郎之《現代的世界作派文壇(二):最近的日本作家》(1929年第一卷第三期)、青野季吉之《論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展開》(1929年第二卷第九期)、本間久雄之《由日本文壇看近來的歐美文壇的優點》(1929年第二卷第九期)等,馮乃超還寫下了《日本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書籍》(《文藝講座》1930年第一期)、沈端先寫了《九一八戰爭後的日本文壇》(《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1932年10月)等,實際上日本左翼文學作品(相當部分已經譯成漢語)大多是「宣傳」而不是文學,左翼文學理論的領袖人物藏原惟人之思想基本上模仿蘇聯。進而,國際上其他樣式的文學和理論少被正面關注、完整的當代世界文學版圖很難再被繪製。
總之,馬克思主義在俄國被成功演變為列寧主義不久,而後在中國普及開來,潘公展聲言馬克思主義「在今日中國仿佛有雄雞一唱天下曉的情景」41,實際指的是中國接受了蘇俄職業革命家所熱衷、俄國不少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放棄的俄式馬克思主義,並且經由對蘇俄新政權、新文藝和列寧學說等不斷譯介、討論,這種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變得生動具體起來,並有了實踐的可能性,而留學歐美的職業知識份子沒有積極關注經典馬克思主義、精通德語並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很少,如蔡元培這位1908-1911年留學德國並認真研修了西方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文明史和民族學問題的學者,回國不久在民國政府教育部長和北大校長位置上推行如何強盛現代民族國家,強調是「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而「世界觀教育乃哲學教育,意在兼採用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之舊學」。由此,胡適之感慨道,「大家都談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了七八個世紀,或兩三萬里路」。
| 註釋 |
| 1 |
丁守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對文學的影響》,載馬良春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討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77-185頁。 |
| 2 |
參見《甲寅》1917年3月29日。 |
| 3 |
《言治》季刊第3冊(1918年7月,署名「李大釗」)。 |
| 4 |
《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9頁。 |
| 5 |
《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85頁。 |
| 6 |
《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3頁。 |
| 7 |
《胡愈之全集》第1卷,三聯書店,1996年,第85-95頁。 |
| 8 |
《胡愈之全集》第1卷,三聯書店,1996年,第100-101頁。 |
| 9 |
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載《言治》季刊第三冊(1918年7月1日)。 |
| 10 |
李大釗:《庶民的勝利》和《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載《新青年》第5卷第5號。 |
| 11 |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載《新青年》第6卷第5號。 |
| 12 |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載《每週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 |
| 13 |
參見《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署名「李守常」)。 |
| 14 |
參見《曙光》第2卷第2號(1921年3月,署名「S.C」) |
| 15 |
參見《晨報》1919年2月20-23日(署名「守常」)。 |
| 16 |
關於五四接受馬克思主義問題,詳情請參見李澤厚先生:《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載《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146-209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 |
| 17 |
楊東蕙:《本國文化史大綱》,北新書局,1931年,第493頁。 |
| 18 |
《李大釗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2頁。 |
| 19 |
以上文章請參見《東方雜誌》1924年2、6月號。 |
| 20 |
《李大釗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41-642頁。其實,陳獨秀在《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嚮導》週報第184期)中也有同感:由列寧革命聯想到中山先生要建造先進中國的革命。 |
| 21 | | |